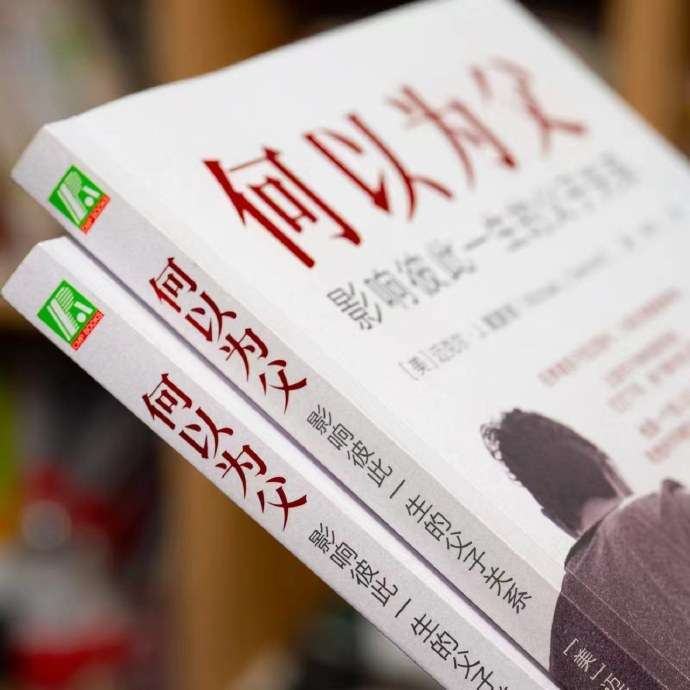开封【千策悦读】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身的父子关系︱童年中期:鼓励孩子拥有掌控力 . ...
|
在迈克尔·J.戴蒙德的《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中,童年中期(6-12岁)被描述为父子关系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父亲的角色从早期的保护者逐渐转变为引导者,其核心任务是帮助孩子发展**掌控力、胜任力以及骄傲感**。本文将从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及深层意义三个维度,系统梳理戴蒙德对这一发展阶段的深刻洞见,并结合个人反思探讨其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童年中期的心理发展特征与父亲角色的转变 童年中期(6-12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潜伏期",是儿童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和道德观念快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戴蒙德指出,这一阶段的男孩开始从"奇幻思维"转向更具因果关系的现实性思维,他们的大脑结构日趋成熟复杂,能够运用更高级的思维方式处理信息。这种认知跃迁为父亲参与教育提供了独特契机——不再是简单的照顾者,而成为孩子探索世界的引路人与能力培养者。 戴蒙德的研究发现,童年中期男孩的内心世界常常"充斥着各式各样情感的骚动",这些感受有时会"一股脑地袭来,变得难以驾驭"。父亲在此阶段的核心职能,是帮助孩子学会**情绪调节与自我管理**,这是掌控力的心理基础。与母亲通常采用的向心性能量(将孩子引向内在)不同,父亲往往以离心的方式(将孩子推向外部世界)与孩子互动,这种差异化的教养风格恰好满足了孩子此阶段的发展需求。 表:童年中期父亲角色的转变* | 发展阶段| 父亲主要角色| 核心教养功能| 互动特点| |------------|-----------------|-----------------|------------| | 婴幼儿期 | 保护者与安全基地提供者
| 建立安全依恋 | 以身体照顾为主 | | 学步期至童年早期| 玩伴与性别角色示范者 | 促进分离个体化 | 游戏互动增多
| |童年中期 | 能力教练与情绪调节者 | 培养掌控力与胜任感 | 指导性互动为主 | 值得注意的是,戴蒙德强调父亲在此阶段需要发展出"教育和指导的能力",这与传统观念中将教育视为母亲专属领域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研究表明,父亲参与度高的男孩在小学阶段会表现出更高的**同理心与自尊水平**,抑郁概率更低,对性别角色和生命的态度也更加灵活。这些发现颠覆了"严父慈母"的刻板印象,为父亲参与童年中期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掌控力与胜任感的培养路径 戴蒙德提出的"足够好的父亲"概念在童年中期得到充分体现——这样的父亲能够走一条"中道":一方面引导孩子调节情绪并获得对事物的掌控感,另一方面促使孩子**最大限度地接受世界挑战**。这种平衡艺术要求父亲既不过度保护,也不放任不管,而是在安全范围内允许孩子体验适度的挫折,从中学习问题解决技能。 在培养掌控力方面,戴蒙德建议父亲采用"脚手架"式教育策略——根据孩子的能力水平提供恰如其分的支持,并随着孩子成长逐渐撤除帮助。例如,在教授骑自行车时,父亲最初可以全程扶持,然后转为偶尔搭手,最后完全放手,这种渐进式授权让孩子体验从依赖到**独立掌握**的过程。戴蒙德特别指出,父亲在此过程中应当克制立即解救孩子于困境的冲动,因为"度过艰难时刻"的能力正是通过克服小挫折而积累起来的。 胜任感的培养则需要父亲成为孩子的"能力见证者"。戴蒙德发现,父亲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够持续把孩子视为"有着自己内在主观世界的、相对独立的存在"。这种"他者"视角使父亲更容易识别并肯定孩子的**独特才能与努力**,而非仅仅关注结果。例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作时,父亲可以具体评价:"我喜欢你如何混合这些颜色来表达阳光的感觉",而非泛泛的"画得真好"。这种针对性反馈强化了孩子的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 戴蒙德还强调父亲在此阶段应当鼓励孩子参与有一定挑战的**实践性活动**,如团队运动、手工制作或科学实验等。通过这类活动,孩子不仅能发展具体技能,更能体验"尝试-失败-调整-成功"的完整学习循环。研究显示,父亲与孩子的这类互动往往比母亲更具活力与刺激性,更可能采用新颖且难以预测的方式,这对孩子的认知灵活性和冒险精神培养尤为有益。 表:父亲培养孩子掌控力与胜任感的具体策略 | 培养目标 | 父亲行为特征 | 具体实践方法 | 心理收益| |------------|-----------------|-----------------|------------| | 掌控力 | 渐进式放手 | 提供脚手架支持,允许适度风险 | 自我效能感、抗逆力 | |胜任感 | 过程性反馈 | 具体肯定努力与策略 | 内在动机、成长心态 | | 情绪调节| 情感容器功能 | 帮助命名和接纳复杂情绪 | 情绪智力、心理韧性 | 情绪管理是掌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戴蒙德指出,理想情况下,男孩应当能够"在与外部世界磨合的同时转向自己的父亲,学习如何有效应对各种既矛盾又强烈的情绪"。父亲在此过程中扮演"情感容器"的角色——通过自身情绪稳定性为孩子示范如何面对挫折、处理冲突及转化消极情绪。这种言传身教比单纯的说教更为有效,它帮助孩子内化一套情绪调节的心理机制。 健康骄傲感的培育与父亲的心理调适 骄傲感在心理学上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情绪,与单纯的傲慢不同,健康的骄傲建立在真实成就与努力基础上。戴蒙德认为,父亲在培育孩子骄傲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为他们通常更能欣赏孩子作为"个体的独一无二性"。这种欣赏不应表现为无条件的赞美,而应与具体成就相关联,使孩子形成基于现实的自我价值感。 戴蒙德描述了父亲培养骄傲感的一个微妙过程:第一次把孩子抱在怀里时,参与度高的父亲会对自己说:"这个孩子是我,但又不是我"。这种辩证认识使父亲能够既分享孩子的成功,又尊重其独立性。例如,当孩子在足球比赛中进球时,父亲可以说:"我看到你平时训练的坚持今天得到了回报",而非"不愧是我的儿子"。前者将成就归因于孩子的努力,后者则隐含着将孩子视为自我延伸的风险。 然而,戴蒙德也警示父亲需警惕将**未实现的自我期待**投射到孩子身上。童年中期是孩子形成独立兴趣与能力图谱的关键期,父亲需要克制按自己喜好塑造孩子的冲动,转而成为孩子天赋与热情的发现者与培育者。这要求父亲具备相当程度的自我觉察与情绪成熟度,能够区分"我希望孩子成为什么"和"孩子实际上是谁"。 戴蒙德提出的"足够好的父亲"并非追求完美,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和有意识的努力"帮助孩子"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样子"。这种立场要求父亲接纳两重现实:一是孩子能力的局限性,二是自身作为父亲的局限性。健康的骄傲感正是在这种**接纳与挑战的平衡中逐渐形成的——父亲既认可孩子的现有能力,又鼓励其突破舒适区,这种张力恰恰是成长的动力源泉。 值得注意的是,戴蒙德发现父亲在参与孩子教育过程中自身也会经历显著变化:"通过成为一个父亲,通过持续性地养育孩子,一个男人会经历情感、心理、品德甚至是身体面貌上的改变"。这种双向成长特性使父子关系在童年中期呈现出独特的互惠性——正如父亲塑造着孩子,孩子也重塑着父亲。 理论反思与现代父职实践启示 戴蒙德对童年中期父子关系的分析建立在深厚的客体关系理论与现代依恋研究基础上,但其观点对传统精神分析框架有所超越。他批评"父爱如山"的比喻虽试图表达爱的厚重与稳定,却可能被潜意识识别为"对父子或父女双方的重负"。这种批判体现了戴蒙德对文化刻板印象的敏锐解构,为建构更健康的父职理念扫清了障碍。 戴蒙德反对"严父慈母"的二元划分,认为"严肃是对内心深处的轻佻、戏谑甚至色情的掩饰","严父有一张恐怖之脸,可能变成子女一生无法驱散的噩梦"。这一激进观点挑战了东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教传统,揭示了严肃背后可能隐藏的**心理防御与边界不清**问题。戴蒙德主张的父职模型融合了传统视为女性特质的品质:"联结、爱、共情、悲悯",这种整合视角为当代父亲提供了更丰富的人格发展蓝图。 在实践层面,戴蒙德的建议极具操作性。他主张父亲在童年中期应当: 1) 成为孩子情绪的"涵容器",帮助其命名和调节复杂感受; 2) 通过共同活动传授具体技能,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3) 提供适度的挑战与支持,让孩子体验"可掌控的风险"; 4) 给予过程导向的反馈,强化努力而非天赋; 5) 尊重孩子的独特性,避免将自我期待强加于人。 这些建议共同构成了童年中期父职实践的系统性框架。 戴蒙德的理论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在学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许多父亲陷入"成就焦虑",过早地将孩子推入标准化竞争的轨道。戴蒙德提醒我们,童年中期更根本的发展任务是培养掌控感、胜任力与健康的自我价值感,这些基础心理能力才是长期发展的内在引擎。父亲的角色不是教练或评审,而是孩子能力发展的支持者与见证者。 此外,戴蒙德对父子"双向成长"的强调也为父亲自我成长提供了动力。参与度高的父亲不仅更可能培养出适应良好的孩子,自身也会变得"情感更加丰沛,头脑更加灵活,思想会更加开放,并且身体会更加健康,寿命也会更长"。这种互惠效应打破了传统上视父职为牺牲奉献的悲情叙事,呈现出养育作为**人类成长途径**的积极面向。 结语:走向足够好的父职 戴蒙德对童年中期父子关系的探讨,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好父亲"的标准。在他看来,好父亲不必完美无缺,但需具备几个关键特质:能够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在未长大的小男孩;挣脱"纯爷们"的咒语,整合刚强与温情;平衡自我实现与父职责任;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格的灵活性,愿意为爱而改变。 童年中期是播种的季节,父亲在此阶段培育的掌控力、胜任感与健康骄傲,将成为孩子应对青春期风暴的内在资源。戴蒙德的深刻洞见提醒我们,父职不是一套固定技巧,而是一段共同
来自: 开封市志愿者协会 ;原作者: 郑东启 开封志愿者
|
最新评论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